《一步之遥》影评(一步之遥武七独白解析)
- 问答动态
- 2024-01-11
- 76
《一步之遥》影评
即便如此,三部*的表现方式各自不同,《让子弹飞》的过度外显(一种强盗、骗子和恶霸的权力政治割据)与《邪不压正》的刻意内隐(依靠某种记忆上的规训)属于两个鲜明的极端,《一步之遥》则是走在中间灰色地带上的文本,它的开放性和如履薄冰的状态,让它在深度和讽刺力方面走得更远。

或者说,马走日更像是只有一步之遥的「民主、真理或者至善」,是四种话语*人所失落的东西,但这一步之遥却也「触不可及」,因为那些稳定的幻象随时都能被马走日戳破——就像权力的蠢像、知识的虚伪、歇斯底里的无效以及分析移情的失败。
姜文调用*史资源对《阎瑞生》的重写,意味着一个失落的文本终究能够抵达它的目的地。这种抵达恰恰是《阎瑞生》如何变成《*毙马走日》的,也就是项飞田所说的「改写历史的两根柱子」,一根是通过马走日扮演马走日来留下历史的「影像证据」,另一根则是以*毙马走日完成「律法*」。
最后是以武大帅、武七、项飞田等人结构的以军队、警察为力量的「主人话语」,这是一种霸权话语,是「*杆子里出政权」的话语,是逼迫人朝着猴子「逆向进化」的话语。但由于权力根本上是「无人称的」,所以这些人实际上只是主人权力的「*」,作为*他们呈现出的是类似于「NewMoney」的绝对蠢像。
这是姜文一贯政治话语的「激进重写」,但伴随它的还有一种「文化话语的激进重写」,这种文化话语也指向一个对象a,也就是中国*史上那个最重要的失落文本——最早的剧情长片《阎瑞生》(1921)。
一步之遥武七独白解析
姜文当然希望他的这些以荒腔走板包装的隐喻能够得到观众的「应答」(当然过往的应答也大多是一种错答、一种误解),但实际上这种操作恰恰验证了某种大众性麻痹,这必然是「一步之遥」的真谛,这一步之遥,看起来很接近,却终究是最难以被戳破、被洞穿的民智隔板。
通过事后性的回溯,人们自然不难发现《一步之遥》中的密集能指,这些讽刺指向民国军阀、总统制、汉*、教育机构和宣传机构等等(部分好事者甚至能给出严格一一对应的中国近代史图谱)。然而仅仅依靠这样的能指与所指应对,尚不足以为《一步之遥》翻案。
这种脆弱和虚空,一方面是因为历史文本的缺失和存疑——不止是《阎瑞生》,中国最初的*文本都没有留下来,也就让文献考古成为一个可以进行想象性描述/任意性重写的巨大黑洞。
《让子弹飞》是姜文迄今为止商业最成功的*,叫好又叫座,这些年一直被网友反复讨论其中的各种深意,台词金句更是风靡网络。而最近的一部《邪不压正》虽不算姜文最成功的作品,但讨论度、票房、口碑都不低。
对吧?姜文除《一步之遥》之外的其余导演作品,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成功之作,只有它算不上。所以从公众的角度来评价,这就是姜文导演生涯唯一的失败之作。
一步之遥有哪些隐喻
他的奇妙点在于同时拥有过剩的男性荷尔蒙和过剩的孩子气,但这两者在根本上并不矛盾。按照*分析的说法,一个人无能为力的人会将自己倒置为「无所不能」,这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之绝对内核。
对姜文来说,*是做梦的艺术,是讽刺的艺术,更是穷奢极欲的艺术——如果梦幻和讽刺是他*的一贯常态,那么2014年的《一步之遥》就将某种穷奢极欲做到了机制,它的铺张浪费和近乎烧钱的奢靡伴随着他最初的踌躇满志,但*上映后的失败,让姜文在幕后哭得死去活来,也证明他仍是个「孩子」。
如此,《一步之遥》就成了对一个病号(也许是姜文自己)的*分析报告,在其中武六站上了导演/分析师的位置,她一直在总览全局、洞若观火,能分辨马走日说的哪些话是真话,哪些话又是假话。
当然,对象a是原初失落之物,是被回溯性构想出来的欲望-成因,所以它一开始就不存在——它只是一个空位,对它的追逐和绞杀所证明的是政权和历史本身就是虚妄的存在,是对真理的实质谋杀和埋葬。
正是凭借这种话语的技法,*的叙述成功地从外部翻向了内部,正是通过将马走日处理为这样的对象a(欲望-成因),我们才能借助马走日的眼睛,形成这样的「内在凝视」(这一方法是曹雪芹《红楼梦》的精妙之处,姜文后来在《邪不压正》中提及曹雪芹也绝非单纯地亵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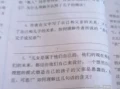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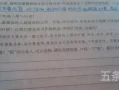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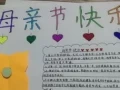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