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许纪霖教授(许纪霖的学术水平)
- 问答动态
- 2024-02-21
- 130
如何评价许纪霖教授
确切地说,到80年代后期,市场化就以商品经济的形式出现,知识分子内部已经开始分化。最大的转折出现在1992年,发生了整个社会世俗化的大转型,人们的心态都变了,变得现实很多,理想主义开始衰落。社会发生急遽的变化。90年代的分化是买不买股票,近十年的分化是买不买房。通过股票和房产两波原始积累,原来都在同一个水准的一代人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层,不仅是资产,更重要的是心态的变化。
这代知识分子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仍然在现实中书写着自己的骄傲或耻辱。新*知识分子开辟了何种*传统?将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历史遗产?在人生进入收官阶段的我们这代人,或许都应该忙里偷闲,静下心来想一想。历史将会浓墨重彩地为我们记上一笔:或者是光荣与梦想,或者是耻辱与庸俗。
我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入学的77级大学生,同学里面大部分是老三届,他们塑造了我们那届学生的主流风格。我当年只有20岁出头,属于红小兵一代,在77级里面是年龄最小的之一,比较边缘。由于身在庐山,又处于边缘,有些问题反而可以看得比较透彻。
许纪霖注意到,近年来无论是大众读者还是学界内部都渐渐出现了一种声音,认为海外中国研究的价值有限,提倡本土化的理论,他把这种认为西方观点不值得讨论的声音概括为“西学原罪论”。他认为这是一种很偷懒的批评,甚至称不上是一种学术批评。因为学术研究不是奥林匹克竞赛,存在“孰优孰劣”,良性的学术交流应当是对所有研究保持好奇开放的心态,什么都读但绝不迷信,“吃百家饭,采百家花,最后酿成自己的蜂蜜。”
许纪霖的学术水平
中国研究则始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1939年,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费正清与历史学家、日本问题专家埃德温·赖肖尔一同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东亚文明课程;1955年,
才发现西方学者的研究课题、使用的资料和挖掘资料的方式往往能带来一些新的认识。“有时候我们是‘身在庐山’,有些问题不一定能够意识到,而西方汉学家作为他者,看中国的问题甚至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
在谈到中国以外的学者对有关中国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的学科时,我们往往会用汉学(Sinology)或中国学(ChineseStudies)来称呼。
“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借鉴欧洲,对日本也有借鉴。此外,他们可以把其他学科的好东西吸纳进来。但是不要以为中国学者在这部分是缺席的。中国的学者,包括晚清民国时期和一些中国当代学者也都非常擅长倾听、理解、接纳。美国的中国研究之所以这么强,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他说。
许纪霖与许倬云
许纪霖从问题意识和叙事方式两个角度阐述了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价值。首先,国外一些学者也许在史料挖掘方面未必有新意,但他们有突出的问题意识。他注意到,中国学生在研究时往往遵循“以论代史”的传统研究模式,先看资料,论从史出。这样的研究方法固然也能做出好的研究,但也有很多资料虽扎实、结论没有任何新意的平庸之作。
王笛认为,当下我们对历史学的理解建立在西方现代历史学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无法回避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对海外中国研究,哪怕是汉学经典顶礼膜拜,而是应该用批判的态度去广泛阅读。“当西方学者在研究美国史、欧洲史的时候,或者日本学者在研究日本史的时候,也引用我们中国学者对中国史的研究——到了那个程度,可以说我们的历史研究是真的走向了世界。”
另外一个转向是学界对历史的理解出现了重大变化。“过去我们总是相信历史有真相,这个真相是唯一的。现在很多中国的历史学家依然相信历史有客观真相,历史学家的唯一目标就是通过发掘史料,揭示这个真相。上世纪80年代以后,历史本质主义被破除,对历史了解越深入越会发现:在这个复杂的世界,已经发生的历史对后人来说是开放的,可以作多元的解读,不同的史料可以整合成不同的真相、不同的图景。”
王笛于1991年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之后每次回国,“海外中国研究丛书”都在他的购书单上。作为研究日常生活的历史学者,丛书中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给了他很多启发。这本1950年代首次出版的作品,到了1990年代几乎仍然是西方研究中国日常生活的唯一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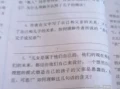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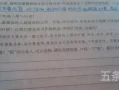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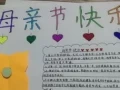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