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墓被掘(海瑞后人现状)
- 问答动态
- 2024-05-16
- 98
海瑞墓被掘
海瑞是理学家丘濬的脑残粉。在明朝文人集体堕入虚无主义邪教思想和唯名诡辩逻辑清谈的大环境下,显得非常耀眼。

新世纪“讲史”中呈现出的晚明想象,虽是帝王将相的故事,但选取的都是普通人关心的内容,且讲述方式通俗易懂。这些内容,与其说是晚明的“遗产”,不如说是满足新世纪大众所需的“创造”。通过对“社会法则”与“人生智慧”的展示,“讲晚明”有效地建立了历史想象与大众的联系,做到了“从历史中来,到大众里去”。
问题在于具有“民族遗恨”特质的历史时段并非只有晚明。其他的历史时段,特别是晚清的屈辱史,可能更加深入人心。那么,为何不是晚清,而是晚明在新世纪成为一种历史热潮?
但在央视节目播出前的问卷调查中,有的观众并不知道袁崇焕是谁,栏目组认为“这会影响收视率”,商量将片名改为《明亡清兴六十年》,开讲篇目仍是“袁崇焕之死”。参见阎崇年:《袁崇焕传》(修订本)后记,*:中华书局,2016年版。
在新世纪“晚明热”中,“我”的历史想象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对晚明历史人物的争论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关于袁崇焕形象的争论。在纸质书、电视和网络三种媒介形态中,袁崇焕形象存在差异。
海瑞后人现状
这类小说的情节模式一般可概括为三个阶段:1主角穿越到晚明,了解环境,规划未来。制造机会,或经商,或从军,或治国。2主角得到机会,逐步执掌权柄,开展行动,具体包括制度改革、军事斗争,进行原始积累与殖民扩张。3成功改变晚明历史。主角或在封建体制内取皇帝而代之,或位极人臣,或建立君主立宪体制,成为该体制的守护者,或直接退隐海外。
“讲晚明”是古老的“讲史”传统在媒介融合时代转型的产物。“讲史”是指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为依据的讲述,“讲史”源远流长,从先秦到宋、元,逐渐演变为职业化的活动。7后来,历史演义小说逐渐替代了口头的“讲史”。到了21世纪,“讲史”传统则借助新媒介得以“复活”8。
代表成果有朱水涌的《社会鼎革与文化转型的历史呼应——谈90年代反映明清时期的历史小说》(《福建*》1999年第1期)、吴秀明的《当代历史小说中的明清叙事》(《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林云的《论90年代长篇历史小说中的明清叙述》(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4[德]西皮尔·克莱默尔:《传媒、计算机和实在性之间到底有何关系?》,选自西皮尔·克莱默尔编:《传媒、计算机和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孙和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刘复生:《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海瑞遗物
在新世纪,研究和宣传袁崇焕较多的是历史学者阎崇年。2006年,他出版了《袁崇焕传》(中华书局)。同年,*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邀请他去讲《袁崇焕》30。阎崇年对袁崇焕的评价极高,认为“袁崇焕以陨星的悲鸣与光亮,划破君主专制沉寂与黑暗的天庭,换来千万人的智慧与觉醒。”31
7楼含松:《从“讲史”到“演义”: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历史叙事》,*: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3、34页。
晚明1想象自明亡之后便已产生,它犹如明月,在不同历史天空投下了纷乱迷离的重影2。新世纪以来3,中国大众文艺领域掀起了一股“晚明热”。其形态多样,既有纸质出版的历史非虚构作品,也有历史剧和网络历史小说;其制造者甚众,有专家学者,亦有业余的文史爱好者;其内容丰富,有帝王将相的风云翻涌,更有小人物的“穿越逆袭”。那么,在新世纪的天空里,晚明究竟有几重投影?这些投影反照了新世纪大众文艺的哪些特质?
罗玮认为,“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观点与20世纪日本右翼历史学家的“元清非中国论”有密切关系,“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提供舆论支撑而臆造出来的说辞。”见罗玮:《驳“崖山之后无中国”说》,《历史评论》2021年第4期。一些狭隘民族主义者在大肆宣扬“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观点时,无形中也变成了自己所厌弃的“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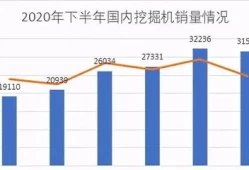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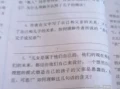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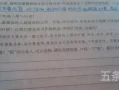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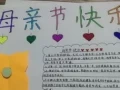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