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苏里万圣书园(刘禹锡文化广场)
- 常识资讯
- 2024-05-26
- 137
刘苏里万圣书园

如今,我住在离万圣书园不远的地方,每周都徒步去万圣书园看书、买书。不时会听到刘苏里老师在书店里的“醒客咖啡”和朋友聊天或接受采访。
刘苏里:我的每个阅读谱系是慢慢形成的,我不追求专业性,也做不到。对我来说,发现填补问题空白的书籍对我更加重要。
我的阅读都是问题意识引导的,一段时间阅读一类书,把散落在书房里不同角落的这类书搬到一起集中来读。比如俄乌战争,这时候我们不得不关心这个问题,于是集中读了很多关于两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的书籍。
刘苏里老师1979年上大学,1993创办以学术书籍为主的万圣书园,是30年来*最重要的书店地标,也是每个爱书人心中最不可或缺的*圣地。
刘苏里:我的私人阅读和购书,主要是非公共领域的,完全跟个人兴趣有关。但是做书店,就不得不面对公共阅读的层面,当然,这里也会有我私人阅读的选书品位在里头。书店选书,对我而言是一种职业性阅读,翻阅式的,一本书两三个小时解决问题,至少做到“知其然”,不算真正的阅读。
刘禹锡文化广场
年买了现在这个房子,是第四个阶段。第一次有了一个固定的家,大量的书云集过来还是放不下,书店库房里还堆着很多。对于读书人而言,固定而长期的住所,才能慢慢形成书房的性格。
刘苏里:可以这么说,也并不完全。上大学后我是饥渴式阅读,凡是带字儿的都看。没人点拨,看书不挑,生冷不忌。上世纪*十年代的确是西方引进的著作有更大吸引力。我看过一本类似年鉴的书,记载了1978年5月,国家出版局组织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一次性投放市场1500万册,瞬间售罄。*各主要新华书店门市同时发售《哈姆雷特》《希腊神话和传说》《一千零一夜》《家》等作品,哄抢之势现在无法想象。
刘苏里:书房性格表现的是书房主人阅读兴趣和品味,而不是摆设或收藏。止庵兄来看我的书房说:“品质不高,什么书都往里放”。这可能跟我和焕萍的性格有关,跟我们多年开书店有关,因为不能只读自己喜欢的,还要兼顾其他。书太多,二层、三层都堆满了书。这样码书的结果是,过一阵就要发一次疯,因为想找的书找不着。
我认为最后一批可以称之为公共阅读的书应该是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和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但还达不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人们读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那样的热度。这本书对知识阶层影响很大。
最近还重读了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对我触动很大。茨威格所谓的“昨日的世界”是什么时候?是1815年至1914年,这一百年的承平时代,欧洲几乎没有战争,成为欧洲大发展最重要的一百年,之后的一战、二战,文明进程受到极大挑战。想想百年承平是什么概念?它不仅是个和平年代,更是一个西方生活方式得到丰满、固定成型的年代。茨威格的潜台词是,它再也不会回来了。
万圣书园老板
还有更多问题是自己一直关注的,有些甚至持续关注几十年。像对美国、日本、英国等几个国家的关注;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关注;对政体转型、人群命运等问题的关注;对贸易、战争、*、婚姻等人类共同的命运问题的关注等等。
刘苏里:书房是我和夫人张焕萍共同建设的,她也有大量收集,文学艺术宗教作品为多。我个人的积攒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研究生毕业时是第一个阶段,当时分了一个40来平方米的房子,把大学七年攒的书集中到一起,第一次有了一个集中放书的地方。
美国历史学家阿德尔曼的《入世哲学家》是我以前读过最近又拿出来重读的书。这本关于德国思想家赫希曼的长篇传记,叙述了赫希曼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从未动摇过信念。同时我又找出赫希曼的《自我*的倾向》和《退出、呼吁与忠诚》,这两本书很好诠释了我们在面对不公的时候,每个人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给出了赫希曼式明确而合理的*。
刘苏里:对万圣书园的未来我还没想出满意方案。包括我家里的这些书,它们的归宿也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问题。焕萍一直有一个想法,做一间图书馆式的“学术旅馆”,实行会员制,有住店学者和作家,举办学术沙龙、读书会,让这些书在另一个层面发挥作用。到那时,我们得真正退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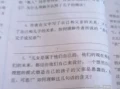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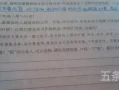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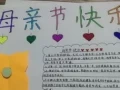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