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 浦东美术馆(刘香成摄影展上海)
- 问答动态
- 2024-03-19
- 150
刘香成 浦东美术馆
作为浦东美术馆开馆以来的第一个摄影展,本次展览是刘香成有史以来展出体量最大的一次,也是其首次扩至全球视角,为中国观众带来摄于中国之外的作品。更打破过去以事件和年份为线索的策展方式,采取全新展览规划,第一次着重摄影语言,从视觉文化的要素提炼其摄影手法要素,并展示后者在不同事件和描述中如何发生作用。本次展览由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出品,浦东美术馆举办。

“在此之间,我遇到过许许多多的沮丧、挫败时刻。幸运的是,创作这件事一直带给我安慰,让我觉得现实中的一切烦恼都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坚持我的信念,而不是屈服于现实。我渐渐意识到,信念能驱使一个人去做任何事来实现他的梦想,没有一丝后悔。”
从社会风貌的进入,到更为内敛的语言的转变,起码在画布上,曾梵志变得更自由了。“我同意这个的看法,”他说,“且更同意塞尚的看法——画什么不重要,怎么画更重要。”展览里一张作品保留了绘画时周边的痕迹,画笔和颜料在狼藉中,挣脱无意义的语法铰链,肆意张扬,想不到那双干净、细嫩到秀气的手,会在这里一尘不染,其力度之大,会让画笔折断。这个过程必然是不会被思索的,就像行动绘画,自动写作以及某种酒神式的体验。
近几年,他几乎不露面,那个总是出现在媒体封面的名流形象已然成为了一种过去式。当然,尽可以说,如今面对公共层面的审慎是一种自我保护。然而不同的是,这种沉默,早已内化在了从不高声语的工作氛围中。
刘香成摄影展上海
浦东美术馆的展览主题虽然名为“过往与此刻”,但实际上,曾梵志不怎么回头看。“除了肖像画一直在创作,一个系列都通常是10年8年后就会走到另外一个阶段了。一张画,别人说画得太好了,你再整一套,我自己也没兴趣,除非是我觉得有一个新的想法和点子,又有某种好玩的东西在里面,我愿意去尝试一次。如果是完全是沿路再去走的话,我可能就对两边的风景就没兴趣了。”
在我们到访工作室的一个月后,曾梵志的展览“过往与此刻”就要在上海浦东美术馆开幕。他昨夜喝了酒,今天来到工作室咽下一口咖啡的时候,眼球里还能看到血丝。他所站的地方,是一个刚被修好的空间,与他一直所用的工作室隔着院子相对,卷起帘子,窗明几净。几块从河南*找的石碑被埋在了地下,在上午天光合适时,几块长方向的天光会洒在碑前。
现在,曾梵志说他对这个世界谈不上什么看法。他说自己写不好也讲不好,自然也不会愿意越过绘画去做一个布道者。有人建议过让他自己录音,记录下灵光片语的思绪,但他不习惯。一副绘画如何在这个时代让人感到临渊一般的屏息,又是如何在进入眼球的*后给予崇高的体验,是否真的有如神启一般的戏剧时刻降临?谁也说不清楚,包括曾梵志自己。
而这种说法对艺术家最不公平的地方就在于,它忽略了那些面对画布的海量时间和上万支画秃的画笔,忽略了艺术家在日复一日中究竟如何水滴石穿。
浦东美术馆门票预约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绘画既总结了我眼睛里所看到的,也反映出我的幻觉,既真实也不真实,既抽象也具象。长期以来,我一直在尝试用一种高度概括的方式来反映我的细节化的感受,我也同时会被这样类型的作品所打动。”
曾梵志转动着雪茄,用的是跟他绘画的同一双手。他没有讲话,只是低头,在听完了诸如“你怎么看待成功艺术家?”的问题后,不置可否地说:“这我也回答不了啊。”然后,拿起金属光泽的点烟器,用火燎起转动的雪茄,即使是在室外的天光里,还能清晰地看到点亮的烟丝在簇中摇曳,忽明忽暗。
在来到*后,曾梵志也曾说过,在武汉其实除了书,什么都没有。1980年代的中国艺术大环境里,艺术创作有着各种规限,乡土、风情、教化的主题,写实、追模笔触,都是主流。忠于自我,以个人情感出发建构他的艺术世界,所以他去看德国表现主义的作品,追寻自由表达的笔触。他是那个能静下心来在自己的书房写小楷的人。
在上一个系列“抽象风景”的几幅作品中,有些局部的处理让他觉得很有意思,于是他逐渐把这些细节进行放大,并且开始在肌理、构图、色彩等很多环节上进行测试。“这个系列还刚刚开头,后续我也很期待它会如何发展。至于绘制的过程,在展览开幕前,曾梵志缄口不言,他说:“还没到讨论太多的时候。”“我觉得创作逻辑上来讲应该是更缜密了,但还是维持了自己长久以来的视觉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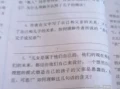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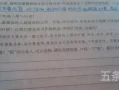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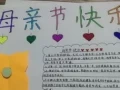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