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导演的经典作品(许鞍华导演在*地位)
- 热门分享
- 2024-04-28
- 97
许鞍华导演的经典作品
作为导演,许鞍华在*影坛上有着其特立独行的地位。她对类型片技巧的圆浑掌握,令她无论拍摄惊悚片、论理片、武侠片以至纪录片,都挥洒自如。

难得的是在商业市场的考虑下,她的多部作品仍渗透着浓浓而共通的作者信息:对过去历史的执迷、对飘泊人间的关怀怜惜、对个人与城市变迁的重视,使她的作品成为*影坛上,罕有能平衡个人言志与类型取向的极佳示范。
无论是借倾城传奇抒发末世感性,还是罕有地以基层运作故事背景,甚至以重现经典去写民族情,或是淡然低回地作自传,都能得心应手、言之有物。
许鞍华的导演生涯可以追溯到1979年,当时她执导了自己的首部剧情长片《疯劫》。这部*以传统的民间故事为背景,通过讲述一个关于爱情和命运的故事,展现了她在导演风格上的独特之处。这部*在上映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让许鞍华在*圈内崭露头角。
作为纪实爱好者,我惊喜地发现有一些“彩蛋”出现在他那台有些年头,已经满是磕碰伤痕的MacBookair上。这个摄影师的黑白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二十来岁的杜海滨、贾樟柯、赵已然、梁龙,出现在铁路沿线,在绿皮火车接口处抽烟,慢门记录曾经那些“游民们”年青的岁月。
许鞍华导演在*地位
时过境迁,等到了《诗》,还是那个熟悉的配方。古稀之年的许鞍华,在纪录片中的呈现,对身份和城市境遇的挖掘,仍是那个“老文青”的身影。她穿着深色棉麻长裙,桌边放一包莫吉托的*,和诗人对坐,在他们的工作室里、家里和茶餐厅里侃大山。
拍摄期间,这个自律又入世的人极度繁忙,那么许鞍华就拍他三个小时的课堂,在一旁听他的诗歌评审,记录他无数次的读诗、讲诗,直到所有的输出结束。我们也和廖伟棠的学生一样,共同听了一节漫长的讲座。他跟学生们从李商隐讲到策兰,讲入世的作家如杜甫、布莱希特;他批评别人的诗歌出现太多大词,如“民主自由”。
讲课的时间久了,一个长镜头太单调,我们就看到摄制组的第二个机位在画面边缘试探,正好就是廖老师在讲策兰的《一片叶子》:“当一次谈话/几乎就是犯罪”。之后的穿帮,更为*,摄影师大摇大摆地从画面中穿过,无数次地提醒我们拍摄的本质。“打倒象征主义!活生生的玫瑰万岁!”
当第一个主要人物黄灿然出现时,许鞍华“套话”问他如何看待*现状。然后地点转向深圳,黄灿然牵着狗,在深圳洞背村的车站目送伴侣上车。
年之后,*森严期间,在台北拍摄,也有其他港人作家出现在片中,可以联想到他们经受的双重压力。片末借来影行者2007年拍过的宝贵素材,“今夜我在码头烧信/群魔在都市的千座针尖上升腾”。廖伟棠出现在皇后码头保卫运动上,身份不断流转。他在现场读诗,他是摄影师,更多时候他是在场的一员。于是,这些林林总总加在一起,构建了他的诗人身份。
许鞍华的代表作
这样的对话,不过分解读,不刻意用力。*开头西西拿着泰迪熊对镜念《旧启德机场》,诗人饮江的《阴谋不沾染世界》贯穿始终,以布莱希特《致后代》结尾,诗人与城市松散自然地串在一起。
廖伟棠说,他认为沟通是无效的。他上课从来不和学生沟通,三个小时的课讲完直接可以变成一本书。既然如此,我们在片中看到的廖伟棠,就是那个单向输出的廖伟棠。拍黄灿然时,许鞍华跟他一起生活,行山,煮饭、饮茶,补裤子。拍廖伟棠,许鞍华则默默在一旁等待。
我想起了《去日苦多》,*回归之时许鞍华拍的一部纪录片。在饭桌上,许鞍华和几位大学同学“吹水倾计”,和老友们拼凑旧时的记忆,北角的街道、五层楼高的模范村、街心公园的树荫,在《去日苦多》里我们看到宏大历史背景下殖民地的过往也是由个体微小的生活记忆构成。
我在此之前鲜少读诗,常常只沉溺在真实影像的一次元中寻找感动,而诗,给我开启了另一个次元的大门,不局限于表达的形式,因为种种表达其实都是在再现真实,超越真实。感谢这部片子,一点也不“文”,也完全不闷,即使是少有文学经验的人如我,也数次泪目,完全感受到诗中、片中想营造的他者和自我纠缠的状态。
这两首诗出现时,是我第一个泪目的时刻。拍*的,做纪录片的,影像工作者们有他们留住城市瞬间的方法。许鞍华善于捕捉从小人物的生产图景,不管是《桃姐》还是《天水围的日与夜》,剧情片用故事起承转合营造社会底层的生活处境。纪录片里,诗人的文字加上许鞍华对其文字所搭配的*画面双重直击,效果翻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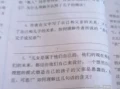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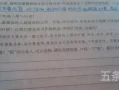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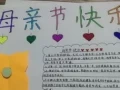







有话要说...